那些曾经占据产业制高点的企业为什么会在此时遭遇重大挑战?那些曾经开创产业未来的成功企业如今为何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扑朔迷离?我们选择了诺基亚、惠普、思科和英特尔四家公司来做深入地探讨和分析,希望能找出理由和原委。
这是四家非常成功的企业:
1、诺基亚一度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一半的份额,如今却在苹果和Andorid阵营的合围中苦苦探索突破之道;
2、惠普现如今仍然是全球营业额最大的IT企业,但是在云计算和IT服务领域,它显然没有做好转型的充分准备;
3、思科一度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高达5400亿美元,现在来自亚洲企业的挑战日益强烈;
4、英特尔曾经主导整个PC产业的发展,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英特尔穿着正装而来,却发现参加的是一个化妆舞会。”
是这些企业准备不够吗?不是,作为产业制高点的掌控者,他们早早就在为下一波产业变革做技术和产品储备,这些企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能力定义产业未来方向。但是为什么在变革到来之时,这些企业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呢?曾经让这些公司如此成功的企业基因此时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呢?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的诅咒”(Winner′s Curse,又译为赢家的诅咒)。这一概念最先是用于解释为了获得石油、天然气而卷入投标公司的投资低回报情况。提出此概念的专家们注意到,在任何形式的拍卖会上,拍卖物的价值是不确定的,赢家很可能由于支付超过竞标项目的实际价值的价码而遭受惩罚。换句话说,赢家往往因为自己的成功因素(出价高)而最终蒙受价值损失(标的项目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值钱)。
将这个概念置换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中来,可以这么说,那些曾经让这些企业走向成功的基因最终可能成为这些面临困境的决定性因素。
诺基亚创新窘境
9月底,北京国际通信展上人流如织,诺基亚的展台却稍显尴尬:面积小,装潢简单,大部分展品都是老机型,很多还是机模。只有N9是个例外——这款本月即将面世的手机有着炫酷的造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围观,常常是六七个人聚成一圈,只有一人能把玩一下仅有的这台N9真机,其他人只能玩玩机模。“怎么这么抠门啊……”有挤不进去的人嘟囔一句,继而离去。
诺基亚展台不远处,包括HTC、华为、中兴、酷派等新秀的展台就“阔气”了很多,真机多,驻足者也多,中兴甚至抢先发布了首批搭载Windows PhONe7.5系统的智能手机Tania。“在智能手机时代,迟缓的反应机制使其产品和系统在研发上市环节滞后,诺基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易观国际分析师孙培麟称。
其他层面的压力也在蔓延。近两个月中,有媒体关于“诺基亚渠道崩盘”、“为WP7手机上市清理库存”的报道,迅速被转载,并迫使诺基亚出面澄清。北京迪信通公司副总裁金鑫也认为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诺基亚是全球手机制造商中以销定产做得最好的企业,它的多周订单管理机制使其可以预测到下一个月的产品销量,进而调控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清理库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目前问题的本质在于诺基亚正面临一个产品创新的断档期,缺乏重磅级产品。”有诺基亚分销商人士称,尽管诺基亚目前在中低端市场还有大量的非智能机在销售,但危机已经存在。

在最辉煌的时候,诺基亚盘踞了全球手机市场40%的份额,为芬兰政府缴纳了占全国21%的企业税。但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在从2007年至今的短短4年中,诺基亚的市值已暴跌75%,曾一度被传将被微软收购。
昨日因种今日果。2007年当乔布斯将全新玩法的iPhone手机的神秘面纱解下,迎接粉丝们起立欢呼时,诺基亚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早就试过触摸屏,但消费者并不感兴趣。”
事实上,诺基亚提出智能手机概念机比iPhone早了10年,触控技术比苹果早3年,Ovi比苹果App STore早了1年。诺基亚创新部门前主管Juhani Risku曾撰文称,在诺基亚研究院有5000名专业人士,其中有500人极为出色,有着“杀手级的灵感”,不幸的是,他们研究出来的创新方案,最终出现在了对手的手机上。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诺基亚的创新步伐?曾经的霸主为何会陷入如此的窘境?
诺基亚提出智能手机概念机比iPhone早了10年,触控技术比后者早3年,Ovi比苹果App Store早了1年。诺基亚创新部门前主管Juhani Risku曾说,诺基亚研究院有5000名专业人士,其中有500人极为出色,有着“杀手级的灵感”!不幸的是,他们研究出来的创新方案,最终出现在了对手的手机上。
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就曾撰文指出,诺基亚是个追求高效率的公司,成本控制做得很好,但这种“高效率的成本控制思维,杀死了诺基亚该有的创新”。
惠普已失去了灵魂
“如果他能干的时间再长一些,还真没准儿就像郭士纳似的了。”说这话的腾讯公司工程副总裁吴军语气里满是遗憾。吴军指的“他”是在1年前由于与一位女供应商存在私人关系以及一些不当支付行为,而被董事会驱逐的惠普前任CEO马克·赫德——现在的赫德早已成了甲骨文的总裁,数天前,他还在甲骨文全球大会上高调亮相,并发表了主题为“极致创新”的演讲。

吴军在硅谷的家离帕罗奥图只有十几分钟车程。72年前,惠普就诞生在帕罗奥图爱迪生大街上一所房子的车库里。从时间上看,惠普是硅谷地区所涌现出的第一家高科技公司,这也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起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身处硅谷心脏地带的惠普几乎就是硅谷的代名词,这家公司身上集中体现了硅谷所倡导的创新精神、创业热情、开放式合作以及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种种这些,被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不断积累沉淀,并构建起惠普崇尚创新和高绩效文化的成功基因。
以生产销售电子仪表起家的惠普,有着深厚的硬件情结,从根本上讲,惠普其实是家很纯粹的硬件制造商。1999年,惠普剥离其测量设备部门,安捷伦科技由此诞生。这也成为惠普公司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2002年,在前任惠普CEO卡莉·费奥瑞纳的主导下,惠普完成了与康柏公司的“世纪并购”,开始大举进入当时看似是一片“蓝海”的PC市场。
由于地处硅谷腹地,惠普对于创新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并以此为基点建立了公司发展的一套“水平模式”——对新技术潮流跟进很快、广交盟友、拥抱业界标准和合作伙伴。后来又经过数次业务拆分重组,在大的方面做加法,小的地方做减法,惠普由此被“拼接”成为全球产品线最长的IT公司,走上了一条规模制胜的道路。
思科:互联网之父即将远去?
近期,两则关于思科和华为的消息一前一后相互映照。一是,7月18日,思科在其美国官网发出公告称,将裁员约6500人,以帮助公司每年削减成本近10亿美元,裁员人数占全体员工的9%;另一则消息是,10月初华为在硅谷新建部门,并且为此部门调配和招聘1万名员工--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互联网之父面对其来自中国企业的有力挑战者,其现状和未来不禁令人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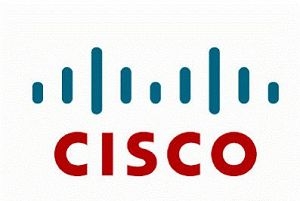
比之微软、Intel、苹果公司,思科公司的成立要“合理”得多:在互联网还没有兴起的1984年,打通各个大学、各家公司的多协议路由器的需求是一触即发的,因此当思科1986年推出第一款产品,它甚至没有做任何市场推广活动就获得了大量订单--可以说,没有思科,就没有如今的互联网。后来的故事超出了它的两位创始人(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两个系担任计算机中心主管的莱昂纳多·波萨卡(Leonard 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 Lerner)夫妇)的预想,为业界的大多数人熟知:思科在1990年便成功上市,市值一度超过微软,高达5400亿美元--思科成为了至今仍然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不过,这位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波动巨大: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曾经让思科的股票价值缩水85%,随后的2001年,思科迎来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裁员,裁员人数达到8500人;后来得益于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和发展,思科走出2001年的低谷。现在,它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英特尔PC之后怎么办
从PC时代的单一终端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多终端,面对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对芯片厂商英特尔来说,却是失去控制力的过程。这就好比它正装而来,却发现参加的是一个化妆舞会。它当然可以就地换装,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合适这个场合的衣服。

其中一件衣服就是超级本(Ultrabook)。这种比PC更轻薄同时不以牺牲性能为代价的新产品形态,是英特尔搭建的从PC到“后PC时代”的桥梁,也是让自己的一个对应的存量市场(PC市场)和增量市场(移动设备市场)流水不腐的连通器。在英特尔负责移动计算产品的高级副总裁邓慕理(Mooly Eden)的讲述中,这种超级本将从目前的轻薄PC到可在平板与PC之间“变换”的形态,再到键盘可拆卸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超级本采用的架构将逐步升级,性能提高,而且可以实现跨平台:不管是微软,Android,Chrome OS,MeeGo,还是WebOS甚至Linux。
PC之外,英特尔谋求发展和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市场,即是嵌入式市场。嵌入式市场由来已久,但对现在的英特尔来说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基于凌动、MeeGo的车载系统、数字标牌是这个市场的主力。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整个全球市场,中国市场在嵌入式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与英特尔近80%的销售额来自海外一致;在这个领域,由于更多类型厂商的加入,使得生态链条丰富和复杂起来,英特尔也在试图拥有更多核心技术,获得主动。而就超级本和嵌入式市场来说,在目前阶段来说,都体现了英特尔重建一个“后PC”生态圈的意图:今年8月,英特尔宣布成立3亿美元的超级本基金,扶持全球范围的元器件厂商、设计师和制造商;而在嵌入式领域,英特尔则把高校资源纳入嵌入式人才的储备中,由OEM、ODM厂商组成的嵌入式联盟,也是借由英特尔的支持在为英特尔获得控制力和未来标准的掌控力出力。
总结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成功的公司却各有各的基因。有的企业是因为技术和产品超凡卓群,有的是创始人或者CEO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前瞻的战略把握能力,有的是卓越的运作流程保证了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产品推出速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每个企业所要面对的“成功的诅咒”也不一样。事实上,我们所要探讨的这四家企业,如今在全球来看依然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对其转型困境原因的探究,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成功的诅咒”这样的陷阱,让企业的发展能够基业长青!







 明基投影机
明基投影机 坚果投影机
坚果投影机 科视投影机
科视投影机 极米投影机
极米投影机 SONNOC投影机
SONNOC投影机 宝视来投影机
宝视来投影机 视美乐投影机
视美乐投影机 当贝投影机
当贝投影机 哈趣投影机
哈趣投影机 WAP手机版
WAP手机版 建议反馈
建议反馈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PjTime
PjTime